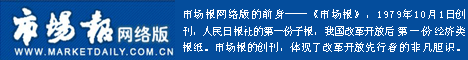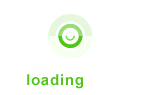网络时代不仅培养段子手,也培养福尔摩斯,这不,春节期间一个关于上海女因一餐年夜饭逃离江西农村的热帖,就被条分缕析,“推理”成了一个网络营销的“骗局”。随后,一批有关乡村问题的文章相继出笼,而且都“有图有真相”,极具现场感,原因无它,春节也是“写手们”一年中最接地气的时候,他们正和江西男一样返乡过节,亲历并感悟着乡村的田园之美与困窘。
我倒是不怎么关心这二人能否走到一起,因为婚姻的事谁能说得清呢?我更关注的则是可能被人们忽略了的根本问题,那就是在社会表面尤其是城市的繁荣奢华背后,整个乡村不可遏制、不可逆转的停滞甚或衰落。
在这个“事件”中,我们只是注意到了上海女除夕夜的逃离,却忽略了年后江西男以“回去上班”为借口的逃离。如果说上海女的逃离还只是个案的话,江西男的逃离 则是群体性的。毋庸置疑的是,无数的“江西男”一定、确定以及肯定会随着返城人流,在正月初六回到他们工作的一线、二线或三线城市,在初七的时候出现在某写字楼里,会见客户、签订合同,抑或喝着香茶或咖啡,刷着朋友圈儿。在江西男们的背后,则是一座座几乎空心化了乡村。
有关当下乡村人员的构成,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形象的说法,那就是“三八六一九九部队”,意即妇女、儿童和老人。而外出务工人员与留守妇女的夫妻生活、留守儿童 父爱母爱及教育的缺失、空巢老人面临的就医养老等问题,也早已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,只是“课题”做了不少,却难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。乡村的生存环境越 差,逃离的人越多;逃离的人越多,乡村的生存环境越差,由此而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。
人们逃离乡村的方式,无非两种,一种是通过考学,一种 是外出务工。考学使精英逃离,务工则使青壮逃离,二者的合力加速了乡村的衰落。在户籍管控严格的年代,人们走出乡村、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只有考学一种。有 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,“锄禾日当午”是没有丁点儿“诗意”的。有位朋友曾经讲过他自己的故事,说他正在地里锄草的时候,得到让他去拿录取通知书的消 息,他随即把锄头一扔,兴奋地跑到地头,连声喊着“到头了,到头了”,颇有点儿范进中举后的“范儿”。这是一种摆脱乡村生活的真正意义上的“如释重负”。 以这种心态出走乡村的农家子弟,几乎没有回归的。考学出来的人会在城市里安家,会让自己的二代或者三代变成地道的城里人,逢年过节时回“老家”看看,煞有 介事地感怀一下儿时旧梦,与父辈亲朋短暂的聚首后,便是匆匆的长久的别离。这也是春节期间各种有关乡村热帖出现的原因。所谓的城里人,“追溯三代以上其实 都是农民”,这话是不错的。在这一庞大的人群中,年长的或已功成名就,年轻的则如江西男一样正在奋斗中,共同点则只有一个,就是都已成功地逃离了农村。
在《中国绅士》一书中,费先生曾言及中国有“叶落归根”的传统,他认为这有助于保持农村人口的较高质量,因为“跳了龙门的人并不忘记他们的故乡,至少当老了 的时候,他们会回来,并尽最大努力,利用在外面得到的特权和好处为家乡谋利。”而这些有能力的人不会永远离开他们的“草根”,“结果不仅是知识分子享受了 农村生活,而且也鼓励了同一地方的其他人。”然而,就在费先生写作此书的时代,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,“现时出身农家在外求学的人并没有回乡发挥作用”,这 不仅是由于他们不愿回去,而且是他们已“回不去了”。
在他们离家时,父母、兄弟和亲戚“不惜卖地和借钱”去帮助他们实现进城的梦,从学院毕 业时,他们却已经切断了和家乡的联系,“在现代大学里,学生学到了西方科学和技术,而且也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体系,这是完全不同于乡下的。”而在家 乡,也无法提供一个适合的工作,让学生们应用所学的知识,因为“中国的大学不是为在农村工作的人准备的。他在大学里学到的是从外国输入的一般性知识”。由 此而造成的结果是农村不断地派出他的孩子,又不断地丧失了金钱和人才。
时光荏苒,七十多年过去了,费先生所说的“不能回家的农家子弟”的情况并没有好转。在当代的乡村治理中,大学生“村官”模式的设计初衷虽好,实行的结果却差强人意,在毕业生无法将其知识适用于其家乡的大环境下,通过考试“考”出来的“村官”,照样是一种闲置的“资源”。
在乡村的变迁中,既要保有曾经的青山绿水,又能让守土的乡民过富足的生活,单纯依靠诸如江西男那样的走出农门的学子是难以为继的。唯一的出路,即是政府在每年的一号文件之外,给予真金白银的投入,只有这样,才会使上海女久留,而乡村也不再仅仅是一个被称作父辈生活的地方。